丹尼尔·卡内曼于200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件事非同寻常,因为他是一位心理学家。具体来说,他是两位心理学家中的一位,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他们着手拆解经济学理论家长期珍视的实体:那个极端理性的决策者,称为经济人。拆解搭档的另一半阿莫斯·特沃斯基于1996年去世,享年59岁。如果特沃斯基在世,他肯定会与卡内曼分享诺贝尔奖,后者是他的长期合作者和挚友。
人类非理性是卡内曼的伟大主题。他的职业生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他和特沃斯基进行了一系列巧妙的实验,揭示了大约二十种认知偏差——无意识的推理错误,这些错误扭曲了我们对世界的判断。其中典型的是锚定效应:我们倾向于受无关数字的影响,这些数字是我们碰巧接触到的。(例如,在一个实验中,经验丰富的德国法官如果刚掷出载有高数的骰子,就倾向于给商店扒手更长的刑期。)第二阶段,卡内曼和特沃斯基证明,在不确定条件下做决策的人,并不像经济模型传统假设的那样行事;他们并不最大化效用。两人随后开发了一个替代决策模型,更忠实于人类心理学,他们称之为前景理论。(正是这项成就让卡内曼获得了诺贝尔奖。)在他职业生涯的第三阶段,主要是在特沃斯基去世后,卡内曼深入研究享乐心理学:幸福的科学,其性质及其原因。他在这个领域的发现令人不安——不仅仅因为一个关键实验涉及故意延长结肠镜检查。
《思考,快与慢》涵盖了这三个阶段。这是一本惊人丰富的书:清晰、深刻、充满智力惊喜和自助价值。它始终娱乐性十足,并经常感人,尤其是当卡内曼讲述他与特沃斯基的合作时。(“我们在共同工作中找到的乐趣让我们异常耐心;当你从不感到无聊时,追求完美就容易多了。”)它对有缺陷的人类理性的视野如此令人印象深刻,以至于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最近宣称,卡内曼和特沃斯基的工作“将会在数百年后被记住”,并且它是“我们看待自己的关键转折点”。他们是,布鲁克斯说,“心灵的刘易斯和克拉克”。
现在,这让我有点担心。本书的反复主题是过度自信。我们所有人,尤其是专家,都倾向于夸大我们对世界的理解程度——卡内曼提醒我们。当然,他自己警惕过度自信的危险。尽管他和特沃斯基(以及其他研究者)在过去几十年声称发现了所有这些认知偏差、谬误和幻觉,但他回避大胆宣称人类本质上是非理性的。
或者他有吗?“我们大多数人大多数时间是健康的,我们大多数判断和行动大多数时间是合适的,”卡内曼在引言中写道。然而,仅几页后,他观察到他与特沃斯基的工作“挑战”了20世纪70年代社会科学家中的正统观点,即“人们通常是理性的”。两位心理学家发现了“正常人思考中的系统错误”:这些错误不是源于情绪的腐蚀影响,而是内置在我们进化的认知机制中。虽然卡内曼只得出温和的政策含义(例如,合同应使用更清晰的语言),其他人——或许过度自信?——走得更远。例如,布鲁克斯辩称,卡内曼和特沃斯基的工作说明了“社会政策的局限性”;特别是,政府采取行动对抗失业和扭转经济的愚蠢。
这样的全面结论,即使作者没有认可,也让我皱眉。而皱眉——正如本书第152页所学——激活了我们内心的怀疑者:卡内曼称之为系统2。实验显示,仅是皱眉,就能减少过度自信;它使我们更分析性,在思考中更警惕;质疑那些我们否则会不加反思地接受的故事,因为它们简单连贯。这就是为什么我皱着眉给了这本异常有趣的书最怀疑的阅读。
在卡内曼的方案中,系统2是我们缓慢、慎重、分析性和有意识努力的推理模式。相反,系统1是我们快速、自动、直觉和大部分无意识的模式。正是系统1检测声音中的敌意,并毫不费力地完成“面包和……”的短语。正是系统2在我们填写税表或在狭窄空间停车时开始行动。(正如卡内曼和其他人发现的,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来判断一个人在任务中系统2的参与度:只需看他的瞳孔扩张程度。)
更一般地说,系统1使用联想和隐喻产生一个快速而粗糙的现实草稿,系统2则基于此得出明确的信念和理性选择。系统1提出,系统2处置。所以系统2似乎是老板,对吗?原则上是的。但系统2除了更慎重和理性外,还懒惰。而且它容易疲劳。(流行术语是“自我耗竭”。)太经常地,而不是放慢速度分析它们,系统2满足于接受系统1喂给它的简单但不可靠的世界故事。“虽然系统2相信自己是行动所在,”卡内曼写道,“自动的系统1是本书的英雄。”系统2似乎特别安静,当你的心情愉快时。
此时,怀疑的读者可能会想知道该如何认真对待所有这些关于系统1和系统2的谈论。它们真的是我们头脑中一对有独特个性的小代理吗?不是真的,卡内曼说。相反,它们是“有用的虚构”——有用,因为它们帮助解释人类心灵的怪癖。
要看到如何,考虑卡内曼称之为他和特沃斯基一起做的实验中最著名和最具争议的:“琳达问题”。实验参与者被告知一个虚构的年轻女人琳达,她单身、直言不讳、非常聪明,作为学生,她深切关注歧视和社会正义问题。然后参与者被问到哪个更可能:(1) 琳达是银行出纳员。或(2) 琳达是银行出纳员并活跃于女权运动。压倒性的回应是(2)更可能;换句话说,给定的背景信息,“女权银行出纳员”比“银行出纳员”更可能。当然,这是对概率法则的公然违反。(每个女权银行出纳员都是银行出纳员;添加细节只能降低概率。)即使在斯坦福商学院的学生中,他们有广泛的概率训练,85%的人在琳达问题上失败。一位学生,被告知她犯了基本的逻辑错误,回应道,“我以为你只是问我的意见。”
这里出了什么问题?一个简单的问题(叙述有多连贯?)被替换为一个更难的问题(它有多可能?)。根据卡内曼,这是许多感染我们思考的偏差的来源。系统1基于“启发式”——回答难题的简单但不完美方式——跳到直觉结论,系统2懒惰地认可这个启发式答案,而不费心检查它是否逻辑。
卡内曼描述了数十种此类实验证明的理性崩溃——“基率忽略”、“可用性级联”、“有效性幻觉”等等。累积效果是让读者对人类理性绝望。
我们真的那么无望吗?再想想琳达问题。即使伟大的进化生物学家斯蒂芬·杰伊·古尔德也为此困扰。作为概率专家,他知道正确答案,但他写道,“我头脑中的一个小矮人不断跳上跳下,对我喊道——‘但她不能只是银行出纳员;读读描述。’”这是古尔德的系统1,卡内曼向我们保证,不断对他喊错答案。但或许有更微妙的事情发生。我们日常对话发生在丰富的未明言期望背景中——语言学家称之为“蕴涵”。这样的蕴涵可以渗入心理实验。鉴于促进我们对话的期望,实验参与者将“琳达是银行职员”理解为暗示她不是女权主义者可能是合理的。如果是这样,他们的答案并不是真正谬误的。
这似乎是一个小点。但它适用于卡内曼和特沃斯基以及其他研究者在正式实验中声称发现的几种偏差。在更自然的设置中——当我们检测骗子而不是解决逻辑谜题;当我们推理事物而不是符号;当我们评估原始数字而不是百分比——人们远不太可能犯同样的错误。所以,至少许多后续研究表明。我们或许并不那么非理性。
当然,有些认知偏差即使在最自然的设置中也明显表现出来。以卡内曼称之为的“规划谬误”为例:我们倾向于高估收益和低估成本,因此愚蠢地承担风险项目。2002年,美国人翻新厨房,平均预计花费18,658美元,但最终支付了38,769美元。
规划谬误是“一种普遍乐观偏差的表现之一”,卡内曼写道,这“可能是认知偏差中最显著的”。现在,在某种意义上,对乐观的偏差显然是坏的,因为它产生虚假信念——比如我们控制一切,而不是运气玩物。但没有这种“控制幻觉”,我们甚至能早上起床吗?乐观者更心理弹性,免疫系统更强,平均寿命比更现实的同行长。而且,正如卡内曼指出的,夸张的乐观有助于保护个人和组织免受另一种偏差“损失厌恶”的瘫痪影响:我们倾向于更害怕损失而不是重视收益。正是夸张的乐观让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谈到驱动资本主义的“动物精神”。
即使我们能摆脱本书确定的偏差和幻觉——卡内曼引用自己克服它们的缺乏进展,怀疑我们能——这是否会让我们的生活更好也远不清楚。这引发了一个基本问题:理性的点是什么?毕竟,我们是达尔文幸存者。我们日常推理能力进化来有效应对复杂动态环境。因此,它们很可能在这种环境中适应,即使在心理学家有些人为的实验中被绊倒。如果理性规范不是人类在日常生活中实际推理的理想化,那么它们从哪里来?作为一个物种,我们在判断中不可能普遍偏差,就像我们在语言使用中不可能普遍不语法——或如此批评卡内曼和特沃斯基研究的人主张。
卡内曼从未从哲学上探讨理性的本质。但他提供了一个引人入胜的解释,什么可能被视为其目标:幸福。幸福意味着什么?当卡内曼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首次提出这个问题时,大多数幸福研究依赖于询问人们对整体生活的满意度。但这样的回顾评估依赖于记忆,这是众所周知的不可靠。如果相反,一个人的快乐或痛苦实际体验能从一刻到一刻采样,然后随时间求和呢?卡内曼称之为“体验幸福”,相对于研究者依赖的“记忆幸福”。他发现这两种幸福措施以惊人的方式分歧。使“体验自我”快乐的东西与使“记忆自我”快乐的东西不同。特别是,记忆自我不关心持续时间——愉快或不愉快体验持续多久。相反,它回顾性地通过体验过程中的疼痛或快乐峰值水平,以及体验结束的方式来评估体验。
记忆幸福的这两个怪癖——“持续时间忽略”和“峰终法则”——在卡内曼更令人痛心的实验之一中惊人地展示。两组患者要接受疼痛的结肠镜检查。A组患者接受正常程序。B组患者也一样,除了——没有告诉他们——在检查结束后添加几分钟轻微不适。哪组遭受更多?嗯,B组忍受了A组的所有疼痛,然后更多。但由于延长B组的结肠镜检查意味着程序结束时不那么痛苦,这个组的患者回顾性地更少介意。(在早期的研究论文中,虽然不在本书中,卡内曼建议实验中B组遭受的额外不适如果增加了他们回来复查的意愿,可能在伦理上是合理的!)
如同结肠镜检查,生活也是如此。是记忆自我在发号施令,而不是体验自我。卡内曼引用研究显示,例如,一个大学生决定是否重复春假度假是由峰终法则应用于前一次决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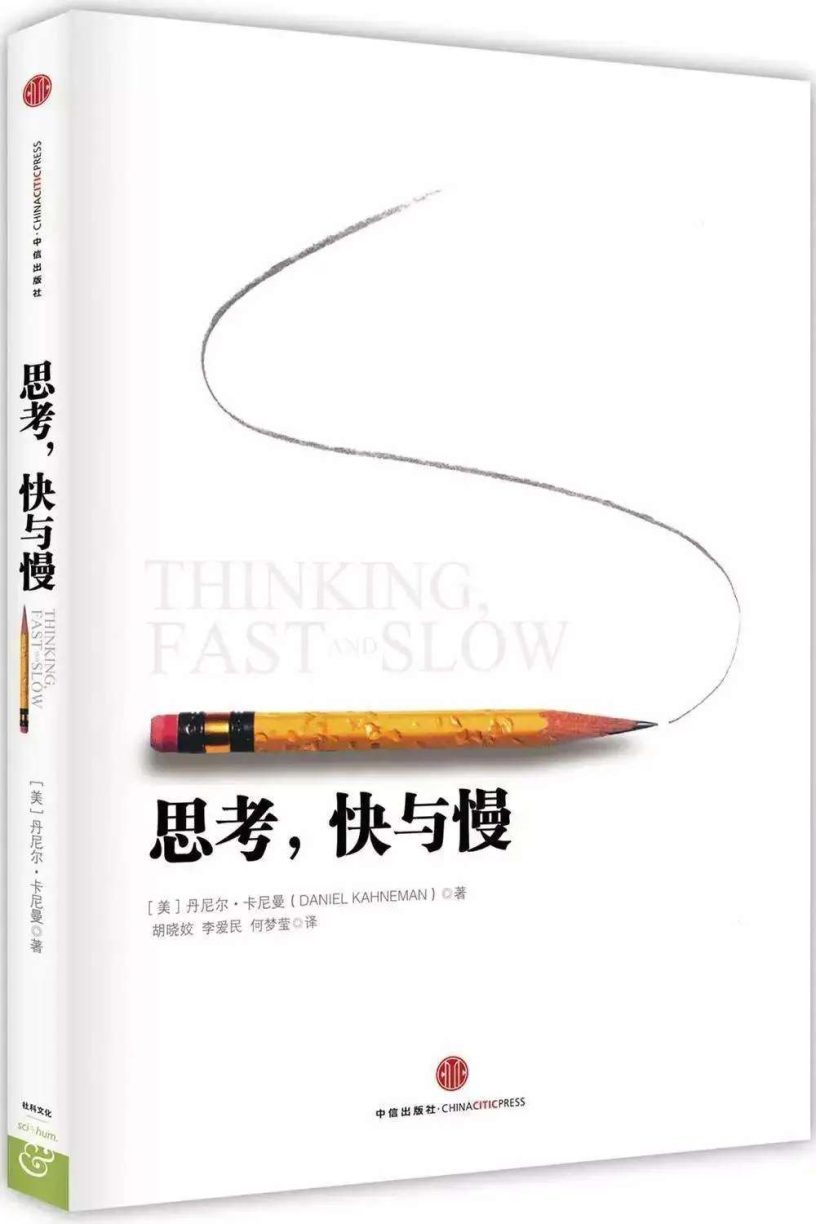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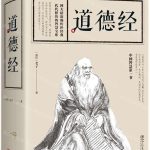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