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一个被迫害的人,不同层级的作家,笔下的功夫天差地别。
不入流的作家,只会干巴巴地说:她是去年被拐来的,天天被婆婆和丈夫打骂,日子苦极了。他们像个宣传员,直接把 “苦” 和 “可怜” 丢给读者,没有任何细节支撑。读者只知道 “她被害了”,却感受不到具体的痛,更别说产生共鸣 —— 这样的描写,就像隔着玻璃看雨,永远触不到真实的寒意。
二流的作家,会加些具体场景。比如写她坐在昏暗屋里,听着婆婆在外骂 “赔钱货,连儿子都生不出”,丈夫推门进来时,她眼神空洞,任由对方扒开衣服。他们懂用情节让读者 “看见” 迫害,用女人的麻木、旁人的刻薄传递悲惨。但这类描写始终困在单一事件里,既挖不透人物内心的绝望,也没把个体悲剧和社会背景勾连起来。读者顶多同情几句,不会追问 “为什么会这样”。
而顶级文学大师,早就跳出了 “写苦” 的套路。他们会写:自她去年被拐来,村子里有样东西渐渐没了声响。起初墙角还偶有呜咽,后来只剩木材般的死寂。如今她眼神发直,见人就垂头念叨 “我有罪过”。村人说她 “不懂规矩,被磨傻了,活该”,小孩朝她扔石子,大人们笑着走过,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而村子,倒日渐兴旺了。
大师的厉害,在于 “留白” 里藏着千钧之力。他们不写具体的打骂,却让你琢磨:是什么样的折磨,能让受害者自认有罪?更刺骨的是,整个村子的价值观早已扭曲 —— 买卖人口成了常态,迫害成了 “规矩”,连孩子都学会了欺凌。这 “兴旺” 的村子背后,藏着多少破碎的人?而这样的村子,在这片土地上又有多少?
说到底,大师写的从来不是一个人的苦,而是一群人的麻木、一个时代的病灶。他们的文字里,藏着比同情更深的痛,比控诉更沉的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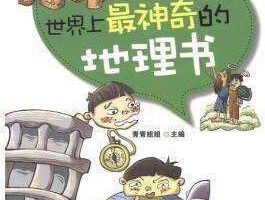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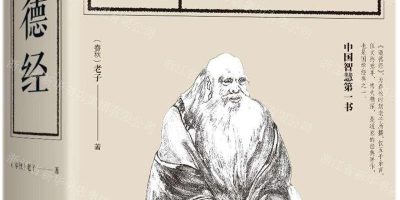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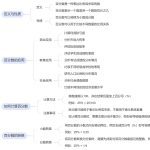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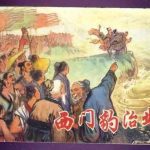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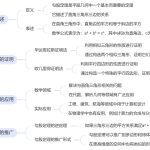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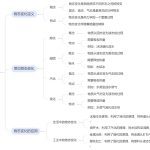

发表评论